登录查看大图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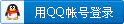
×
本帖最后由 陈维银 于 2024-12-19 16:24 编辑
文革与斗地主(作者陈维银) 前芦家庄故事之二十三 作者陈维银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1966年“文革”也波及我们生产队,先是小道消息传来“文革”的消息。在县城读高三的任兴无,全力学习冲刺高考,高考前一个月全国停止高考,随后任兴无去北京串联,他见多识广,自县城回来后,村里对“文革”感兴趣的几个人,晚饭后靠在陈孝根门前柴草堆上,听任兴无神秘地讲述他串联北京及在县城中的见闻,我也在一旁听的津津乐道。 任兴无还带回来一个神秘的耳塞子,里面有人讲话,还唱京腔,我为了能亲耳听一听,我跟在任兴无身后,任兴无在老房子后面搬砖头,他要我帮他搬砖头,晚上给我听耳塞子。晚上我去他家,几个人在排队等着听耳塞子。耳塞子放进我的右耳,我第一次通过耳塞子听见了清晰的女子京腔。只一会,任天柏将耳塞从我头上抢夺了过去:“小伢嘎听么事煞”。 随后掀起全民开始学毛选的运动,比我大三岁的兰子,异常聪明,没有上过学的兰子,却能熟背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一天下午全大队停下生产,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在老徐溪桥小学操场上,临时搭建了主席台。赵书记讲话后,由兰子上台独自站在会议桌前,高声背诵“老三篇”,先是声音很高,声音渐渐变低,小园脸被太阳晒的通红,她坚持背诵完了“老三篇”。全大队社员们集中按生产队划分,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坐在自带的小板凳,先是静静地听,后来大家也低声交头接耳。 约在1967年,要求各村建忠字台,我们生产队在我家前约50米处,也挑土砌了忠字台,约4米高忠字台的照壁也有模有样,两侧各有一个门,两侧还有大标语,大照壁上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彩色画卷。 文革时期,我们爱国大队组建了一支宣传队,宣传队搞得有声有色,演出水平有模有样,服务道具布景灯具应有尽有,还有吹拉弹唱的各种能人,每个生产队选送一名脱产演员,生产队记工分,我们队选派的演员叫高子美,她可是宣传队里的主角,《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都由高子美出演。 宣传队里有个传奇人物名叫张华伯,张华伯有一定的文化,他能写能画能导演还能演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由他出演,出演时的动作夸张,他演出时精气神太足了。民间对他的评论很多,他当过代课老师,带人在全大队各村各户搜查家谱古书,还将我村任氏宗谱搜走烧毁了,拆庙砸菩萨,挖药材搞药方子,捉黄鼠狼,扎龙船制道具,组织龙船队打地场扮小丑,年老时画符算命扎死人用的祭祀品,讲话时摇头晃脑口喷吐沬星子。反正我觉得他的能量太多了,我们爱国大队宣传队的水准和演出质量及演出场次,远远胜过公社的宣传队,这一切完全是他一手打造的。 宣传队多次来我们村演出,在忠字台上演出过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 演出那天傍晚,我将我家的几个小板凳放在忠子台前抢占好位置,给邻村来的亲戚坐。随后我便跟随任天虎后面,看他将汽油灯如何一步一步点亮,汽油灯可亮了,它上部为灯顶,下部为灯座,内装煤油,园玻璃罩住中间的约6公分长的纱罩,强烈的光源就是由纱罩发出的。灯座上有打气管子,打进空气将空气压缩在灯座,灯座里的煤油从一组小孔中压出,喷成雾状小滴,化为蒸汽,跟空气均匀混合后燃烧,使纱罩发出炽热光亮,纱罩被高温燃后已经是灰烬,但保存好下次仍可使用,二盏汽油灯挂在舞台两头,发出的光亮能将整个村庄照亮如白天。 京剧很多唱词红顺子一学就会,学唱起来有模有样,而我怎么也记不全唱词,更别说唱起来。 我们村也曾组织过宣传队,我、兰子、刘敬华等在任天甲家原来大房子里集中开小会,终于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弄不起来,不久不了了之。 有年放暑假,学校要求各村小学生回村组织起来,每天排队操练和学毛选,我是组长,十几个同村的小学生,每天都在我家西山头集中,由我读毛主席语录,我又觉得我不够硬气,又请贫农张荣喜和高子美当辅导员,他们来跟大家见一个面后也没有时间来了,我们坚持了半个多月又解散了。 一个时间段进行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干活的社员,早晨出工前,集中排队背对忠字台前,由队里的文化辅导员读几条毛主席的语录,然后副队长给社员们分工。中午饭后出工前,照早晨的形式再来一次,晚上息工,大家又按早晨的形式再集中一次。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时,队里六位老奶奶是地主婆子,其中一位精神不好,五位地主婆子一字并排,站在忠字台的前面,面向忠字台低头认罪,后面则是社员排列整齐的社员队伍,他们的子女也都站在他们的身后,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两年阶级斗争抓得紧,所有地主婆家里来客,必须来向我父亲汇报,我父亲是政治队长,我经常中午见地主婆来我家,对我父亲报告:“孝清哥哥,我女儿某某回来了,中午在家吃饭,下午回去。”我父亲回应一声“婶婶、我晓得了”。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天上午约十点,我哥哥跑到赤虎山南替换我放牛,兴冲冲地告诉我,快回村里秀贵家,生产队在开会斗地主婆子,我哥哥那年已经是队里的社员,他参加斗争会是计工分的,因为不感兴趣,所以跑上山替换我放牛。 秀贵家住村后西北角,我一路狂奔,又是下坡,很快到了秀贵家,当我看到快60岁的芦啟余遗孀徐日珍双手被绑在身后,吊在屋架下,下面一张大椅子上又是一个小凳子,一双小脚站在小凳子上,身体颤颤巍巍,下面围坐着一圈十几个男社员,她的大儿子及二儿子也坐在下面,我刚站在门口,她二儿子根寿对着她说:“嫩讲呀,嫩勾结特务,交代呀,不讲再往上吊嫩”。 她大儿子根喜又对着她说:“讲呀,嫩不讲还不是嫩吃苦”。 徐日珍边哭泣边小声地回应,“鹅不晓得歪,他去山上开会鹅也不晓得,鹅要晓得不给他去了歪”。 有人厉声喝道,“嫩不交代,往上拉绳子吊她,看她讲不讲”。 徐日珍背后绳子一紧,身体往上引,一双小脚踮起要离开小凳子了。徐日珍大喊:痛歪,痛死鹅了,鹅讲鹅讲。 吊绳又往下放,徐日珍继续哭泣着:鹅哪晓得煞,不晓得歪……嗯嗯恩。 斗争会在徐日珍反反复复哭泣声中结束,但毫无结果,这也是我唯一一次目睹斗争会的现场。我猜不到她俩儿子当时是什么心态和心情。 斗争会是大队派人来组织的,又叫停产闹革命。有时下雨天也开这样的斗争会,有历史问题的老人都遭遇到开斗争会。 我们村地主老太婆共六位,袁氏是早就受刺激疯了,自然免受一切斗争,其他四位地主老太婆遭遇斗争时,都是到会走走过场,因为这四位地主老太婆为人处事比较善良,子女也跟大多数贫农关系融洽,大家也拿不下面子。 唯有徐日珍平时碎碎嘴,念念叨叨,在队里也没有太好的人缘,大队派人来组织的斗争会,自然会想到她是可斗争的对象,所以大白天停工开斗地主会,她会在全村人面前吊起来被斗争。 任天甲老夫妇是贫民成分,本不是批斗对象,但他本家教书先生任曰澂(字原)先生,在乌山柘塘公社一带教书,文革中首先被残酷斗争,那不是公开批斗,而且成立了专政组,红卫兵小将日夜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往死里整他,还是揪住任氏家族解放前枪支老问题,结果他被整糊涂了,说枪支也许任天甲知道。 大队成立专案组,立即对任天甲夫妇实行关押,任天甲被关押在村里杨满福家三间空房间里,一天晚上由张桂香、张华柏、许哥子等人,对任天甲进行刑讯逼供,将其两个大拇指用牛鞭子细麻绳扣住,吊在屋架下面,这还不算,又找来二块土坯约60斤,用绳子绑好往任天甲脖颈上挂,挂的过程中绳子断了,他们怕出人命,就放弃了。如果挂成功,仅吊二个大拇指在空中的任天甲,当时肯定承受不了,是否会闹出人命还很难说。我小佬陈孝元每天晚上,在那个房子西房间里睡觉,这一过程被我小佬陈孝元全过程看到了,他小佬吓的不敢出声也睡不着。 张桂香、张华柏、任天甲都不在人世了,83岁的许哥子还活着,前两天我去找他求证,他连连否认:“那是张桂香、张华柏二人干的,我只是负责看管任天甲,我可没有参与吊人打人哟。” 任天甲的案子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过了几天就放了任天甲。任天甲被吊被打后,去那里讲理,没有地方讲理,也不敢讲理。 我小时候时常去任天甲家玩,他老太婆见我去了,也不管我当时还是小孩子听懂听不懂,她卷起衣袖,指着她的手臂:“嫩看嫩看,鹅的手臂上的是斗争鹅时,捆鹅吊鹅时的印子,小伢嫩看看,鹅吃的苦遭的罪都没处讲唉。”老太婆一阵唏嘘一阵唉声叹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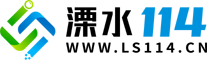




 发表于 2024-12-11 04:37:37
发表于 2024-12-11 04:37: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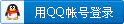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变色卡
变色卡 照妖镜
照妖镜 发表于 2024-12-11 09:40:51
发表于 2024-12-11 09:40:51
 发表于 2024-12-12 15:26:01
发表于 2024-12-12 15:2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