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查看大图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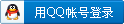
×
作者:唐传全
六十年代末,我从南京到溧水孔镇乡来“插队”。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感到溧水的风俗民情之中有不少独、特、奇的东西,这些风俗民情正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淡化乃至消失。虽说都不是什么“正事”,但对一个县的文史资料,相信多少能起到点“佐料”作用。
溧水话难懂甚于其它县。个中道理我琢磨着有三个原因:一、与普通话差异较大;二、语种庞杂;三、缺少交流、对外影响小。
对第一个原因我是颇有领教的。我插队的当天从乡政府(当时称公社)领导的“讲话”到全村人来望我们这些“城里人”,压根儿就没有听懂一句完整的话。其后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与村人会话也还需要借助手势,那种感觉,与其说到了它乡倒不如说到了“异国”,可见深水话与普通话的差异之大。
其二,语种庞杂也不是一般县所能相比。在溧水且不说当地方言与好几种外地方言交杂使用,叫人难以掌握,即使是纯溧水方言,也有“南北相异,东西迥然”之别;且各地方言还具有新、老派别之分,形成了罕见的“南腔北调、东言西语”的独特现象。尤其是南部方言和西部土语,在吴方言的基础上夹杂着江淮话并保留了古汉语和一些现已很少使用的口语等成份,这无疑增加了溧水方言的庞杂程度。
其三,与源出一脉的高淳人不同,溧水人不善交往,更少有外出经商作贾的。虽地处苏南一域,却全没有“吴侬软语”的吴风;相反,乡人出言生硬,性情耿直而粗犷,也很自尊,即使操“贱业”也决不肯低首下人。还保有“千行万行,种田是上行”的尚耕之风;以及“宁可低头求土、不可抬头求人”的为人之道。即使一县之内,农户之间,早年也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在农村就常听到:“看不到家里烟囱就淌眼水”的自嘲)。这种老死桑锌的封闭生活,形成了长期以来一县之内南北互不通话、东西难成一言的古怪方言现象。
我虽非务农人家出身,可是对一般农业生产劳动工具自信还并不陌生但不管是儿时在苏北老家还是后来北至辽东、南到湖广,各地农具也见过不少,而溧水地区(事实上是“古溧阳区域”含今日高淳、溧阳部分)的农业劳动工具不论是造型、还是使用方法,与别地相比皆有不少奇特之处,还颇有点“古”趣。略举一二为证: 夯,这种常见的生产工具虽有铁、木、石等用材不同和形状大小之异,但大多在其四周以绳子拴住夯体,然后利用人力同时斜拉使夯体受力上抛,再以物体自由下落或等其一定高度后再向下拉索形成反冲力达到劳动效果。而溧水农村中使用的夯,不仅造型特别,其操作过程更是独树一帜,古拙而富有情趣。这种夯取材为一巨石高约尺许四角正方,上窄下宽收坡有度,重约二百余斤。若置于平地之中确象一座缩小了的“金字塔”;又似一枚放大了的古印章。操作时以四根齐眉木棍上下平行交错横嵌在夯体上部沟槽内、绳索固紧,棍端各立一人,位居八方,中有一人领头“喊夯”,所喊词句,既有提示操作人注意事项以便协调一致工作;又有号召大家齐心合力藐视困难的勉励。有的“领头”还能即兴创作,诸如眼前风物的动态场景、过往行人等,皆能有韵有调随口编入,类似于巴蜀的“滑杆文学”。整个操作分三步完成:即领头起声时8个人同时弯腰握把,将夯拎起平身;起声到将了之时,众人一如举重运动员一般挺胸直臂,一气而上,将夯举过头顶;众人一致和声时统一撒把,并把自己的身体偏向与夯体相反的八个方向,如此反复。远远看去:一起一落,一动一静;有张有弛、有劳有逸;人随夯动、夯随人移。加之一唱众和,抑扬顿挫,我初见之时,几疑是一种模仿古代集体性的体育活动。
织布。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社会劳动分工便渐趋集中,所谓的“男耕女织”已是个很古的概念了。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溧水农村竟然还有那么一方“你织布来我耕田”的古俗之地。1968年我插队孔镇乡的广西叶家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这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小自然村,就有六、七台象电影《天仙配》中才能看到的那种织布机。村中老妪少妇均能上“机”织布,有一些所谓“正统”人家十几岁小姑娘也能“唧唧复唧唧”地左右穿梭,以至“五日成一段、半月断一匹”的能手,亦不鲜见,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纺、浣、浆、绣等女红一应齐全。后来村中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才把这一古老的生计灭绝。按理说这应该是现代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前面的“夯”一样,迟早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我又常常发出这样的痴想:要是能有意识地保留一点,将来开发旅游事业,作为田园景观,倒也不失为一大特色。由此又联想到实际上已是绝迹的“砻”,和我曾在渔歌乡仓口村中所看到老式油坊中的石槽巨碾,若能一移入县博物馆中妥为保存,也许能免后人考证之苦。除上述这些几近绝迹和已经绝迹的生产劳动工具外,溧水境内还有一些至今仍普遍使用的农具,也有其奇特之处。
挖锹。溧水的挖锹高不及胸铲宽数寸端呈月牙形状如佛门禅杖,柄为木质,上置一个小横把。使用此锹,技法特别,使用者一手握柄,另一只手握把并置于腹部,屈腿弓身,手撑腹顶,通体向下用力,若操作得法,挖沟开坭、切割土块,锋利无比,外地的锹铲绝难与之匹敌。记得我有一次回到苏北老家,向家人说起这一农具及操作方法时,引得家人捧腹大笑,说我是从“哪国”看来的“怪物”,可见这一农具比较罕见的了。
尖担。溧水地区除和它处有相同的扁担外,还有一种以坚实杂木为本,两头着铁、端呈枪头的“尖担”。我且不说它是否在很早以前可作为防身敌兽、抗匪拒盗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两用之物:单其作用的科学性就使一般扁担所不及。我们苏北人担柴挑草均用普通的扁担,以它从事这些劳动,有以下三弊:一、担物高度不可及肩,不然物体不能悬起,弊在量少;二、扁担吃重后两端下弯担物离地间距便小,逢沟过坎,连拖带拽,还会绊脚,弊在不爽;三、担物与人体间空隙不够,转体换肩,柴草撩面,弊在碍体。而用尖担作同一工作时,不仅上述弊病无存,还有一般扁担无法达到的特殊功用。其使用方法是:把尖担一头插进土中,呈旗杆直立之态,然后将捆柴草的绳索一头结在空中“枪头”之上,并顺木呈L型铺放,以木为抵靠之物把柴草沿木而上,码得高过人顶,系紧绳后照前法再码一垛,垛成横放,人居其间,手持尖担,以其一头插进垛内与人胸平之处,屈腿弓腰,负担于肩、力扛重头,使担成斜刺之势的描另朵,人顺势平身而起。整个过程雄健豪迈,既有力量的造型,又有技巧的应用。文武结合、刚柔并重;一招一式、干净利落,不紧不慢、一气呵成。若担者为力巨之人,数百斤的重担在肩,亦无负累之态,远远观之,赫然如“两山”拔地,悠悠然似“双峰”飘 移,虽凝重而不滞涩,堪称溧中一绝。
三、客入吃饭用手“盖”
溧水人好客,特别是喜庆筵席,主人宴客除劝酒敬菜等与外地共有的待客礼节外,另有“娅饭”一俗,甚为特别。顾名思义,捶者,强迫也。就是在未经客人同意的情况下冷不防往你碗内扣上一碗饭强迫你吃下去。按溧水的娅饭“规矩”,要是饭准确地被人“桠”进碗中,就必须吃下去,同桌之人非但不怪主人,反而以“粮食不可糟;跨个田洼三碗饭…”种种“理由”逼着你吃。我初到溧水时就被捶过一次,而且是一连被娅三碗。记得在被捶第三碗后,凭人怎么“逼”,我也不肯吃,坚拒之下,众人调侃地要我用衣袋把饭装着带回去,真叫人下不了台。虽说我后来知道这不过是喜庆筵间的打趣玩闹而并非是什么“规矩”,但一来为了避免口舌;二来白花花的米饭倒了不吃也着实糟蹋粮食,为此我也学着当地人采用防饭的二手绝活,以手掌“盖”住碗口、从指中“掏”饭吃,或于脆把碗藏于桌下以桌面“盖”住碗,这是我亲自体验到的漂水一怪—客人吃饭用手盖。
四、会“哭”的新娘人敬爱
一般来说,新娘出嫁之时,车轿临门,为人之妇即在眼前。过去的那种依偎父母、弟妹相厮的闺中生活就要成为过去,一时心酸暗暗呜鸣地哭上几声。本为常情,他乡别处亦常有之。但早先溧水农村的新娘“哭嫁”,不只是那种无言的鸣鸣之哭而是要哭出样子来,哭出内容来。我到村中的第二日,适逢村上一户人家姑娘出嫁,那日全村老幼前去看热闹我亦随众夹在其间。只见新娘身着红袄绿裤、足蹬绣鞋,觯不沾土端坐堂中,屋内香火花烛置于几案,那新娘伏案恸哭时呼时诉、时断时续,口中念念有词。我当时因不谙方言,但她那哭中有“唱”、唱中有词及那恸哭之态,实在令人费解。后来居处日久,我才知晓,那恸哭之状并非出于内心,而是“哭嫁”时必须做出的一种公式化的节奏。至于那哭词也有其规定的内容,它要求新人一气流韵地道出对父母未尽的孝道、对未成年的弟妹放心不下等难舍难别之词。由于这种“哭”的形式和内容要求甚高,若平日疏于演练,事到临头断难娴熟。故而那些懂得事理的女儿家便常常背着人暗下“功夫”,一村之中总有那么几个灵秀小姐,把这哭嫁的“套路”演练得做、唱二绝,待到大喜之日便一展才情叫那些看热闹的少男少女们羡慕不已。若新娘是位哭嫁的高手,当哭到动情之处,会赢得村中老少妇女一片唏嘘之声,陪着蓝泪,不时还要劝说几句宽慰的话。那大喜中悲戚的情调,即使是当今上乘的演员,也绝难做到如此纯朴归真。因而往往:那哭嫁时言情二绝的新人到了夫家后,不但被村人视为孝亲淑女、传为美谈,而且更能得到丈夫、公婆的分外敬重。
五、烧锅双手打“节拍”
溧水境内有一种别于它处的土灶—扑灶。该灶设计特别,其烟道垒在锅的前方,这与一般的农家土灶正好位置相反;数锅纵列、也与它灶的横排相异。一户人家仅设一灶一膛、前后二锅,多口的人家也有设三锅、四锅的,但比较少见。此灶使用方法甚为特别,烧火时需一人双手握稻草或茅柴上下不停地扑打。我初见此灶时,觉得新奇,曾戏称“打节拍”,细而察之,原来是利用煽动形成气流向灶膛内输氧以助其燃。由于烟道设在灶膛前端,膛内火苗被“拉”成一条直线,使纵列的几口锅具均能受热,多口人家按灶火前强后弱之理,取前锅烧菜,中锅煮饭、尾锅温水,以充分利用热能。这种灶虽有扑打之劳和易于飞灰之弊,但因其火旺快速,一膛数锅省柴节能等长处,迄今仍有不少农家在延用。
转自巜溧水古今》1993.11第十二辑 |